本文为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林航教授的会议发言,以“文姬归汉:由一幅金代画卷考察女真文化及其身份认同的变迁”为题,对吉林省博物馆藏《文姬归汉图》的绘制时间发表了看法。
《文姬归汉图》(图1),绢本设色,长129厘米、宽29厘米,曾收于清宫,现藏于吉林省博物院,是仅存的少数金代画卷之一。不同于《维摩演教图》《司马犹梦苏小图卷》等其它金代画卷题材所绘人物,《文姬归汉图》形象展现了12-13世纪之交金代女真的样貌。虽然该画没有明确署名,但从画卷上依稀可见的字迹及所绘人物的形象、服饰、装扮等各方面进行综合判断,可知这是一幅由金代宫廷画师于金代晚期所绘的画卷。通过对画卷细节进行分析,结合金代特殊的历史背景,不但可以帮助解析该画的作者和绘制时间,也可由其中所含的金代艺术特征和女真文化元素推断,该特定历史时期中女真文化有了显著的变迁,而女真人的身份认同也发生了微妙变化。


图1:《文姬归汉图》(局部)
绘制时间和画者
画卷前端钤有万历帝“皇帝图书”“宝玩之记”两印,后端款书处有“万历之玺”一印。文姬前方留空处书有乾隆御笔题诗,下注“内府鉴定”四字,钤“神品”“乾隆宸翰”两印,诗末押“比德”“朗润”两个小方印,另有乾隆、嘉庆、宣统诸鉴藏印。画卷左上角题有有一列极为模糊的落款:“祗应司张□画”(图2)。1964年,郭沫若先生诠定为“张”之后已显漶漫之字为“瑀”。至今,虽然高木森曾推测此字应为“茂”,而郑国则认定此字为“珦”,而国内外大多数学者认同郭沫若的说法,认为此画为张瑀所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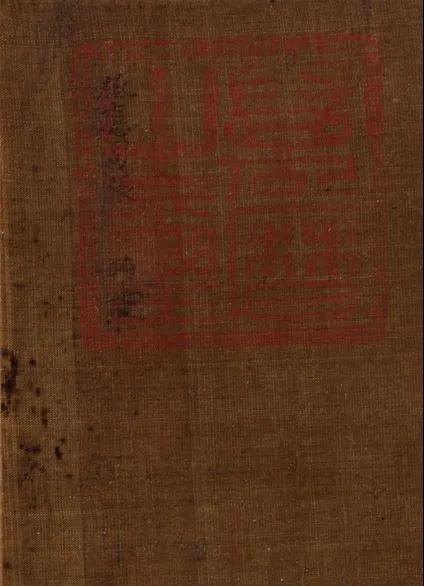
图2:《文姬归汉图》落款
然而通过观察落款题字可知,关于“张”之后究竟为何字,似可有其他解读空间。题字起头三字为“祗應司”,为画师所属机构之名。祗应司为辽代已有,元代亦设,然辽元二代的祗应司只负责监管宫廷建造和相关杂物。而金代时,该机构负责监管宫廷建造和修饰,也管理内廷工艺。据《金史》记载,至金章宗承安元年(1196年),负责绘画和刺绣的图画署也并入了祗应司。由此可知,此画卷应当绘于1196年图画署隶属于祗应司之后。清初学者王士祯曾为此图作诗,诗中称此画为“宋南渡祗侯司张某画”,显然是误读。南宋宫廷为中低阶画师设有“祗侯”一职,但未曾有记载也有祗候司。显然,乾隆题诗中所称“宋人文姬归汉图”,当为错依王士祯之言。
“祗應司”三字其下之字为“張”,落款的最后一字为“画”。“画”上之字的下半部分依稀可见,但整体已模糊难辨。然细观落款可见,在此字和其上“張”字之间有一明显空格,而这个空格足以放下一个字。因此可推断,不论这个很模糊的字到底是“瑀”“茂”还是“珦”,本图的作者名字应该一共有三字,即为“张某瑀”“张某珦”“张某茂”,抑或其它。迄今可知的金代画家十分有限,其中有一人名为张珪(活跃于1150–1161),活跃于海陵王完颜亮统治的正隆年间,绘有著名的《神龟图》。张珪生活的时代早于图画署并入祗应司前至少35年,则《文姬归汉图》当很难为他所绘。考虑到唐宋时期很多宫廷画师都是家传,不排除《文姬归汉图》的实际作者为张珪的子辈或孙辈。
《文姬归汉图》与《明妃出塞图》
文姬归汉题材的绘画在南宋曾风行一时,殆因绍兴十一年(1141年),宋金缔结盟约,次年自北地迎回高宗生母韦太后。基于这桩重大事件,南宋宫廷画师绘制了一系列画卷,包括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的传仇英《中兴瑞应图》(图3)。此外,画师也将该时间与其他相似历史题材相联系,特别是文姬归汉的故事,以此借古颂今,如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传李唐《文姬归汉图》和传宋陈居中《文姬归汉图》《胡笳十八拍》、南京博物院藏《胡笳十八拍》(图4)、波士顿美术馆藏四幅《胡笳十八拍》残卷(图5)等。箇中深意,一方面是迎合上意,博取共鸣,以汉代旧事展现朝野上下皆企盼重复河山、拯救亲旧的心情。另一方面,取材文姬归汉故事,又有借古讽今之意。历史中,蔡文姬归汉时已与匈奴左贤王育有二子,但此二子并未随母南归。而韦太后自靖康之变被掳北去后,被迫改嫁女真贵族,并也育有二子,且此二子亦未南归。韦太后在金国嫁人生子之事,为宋高宗之大不堪。因此自韦后南归后,宋廷便百般掩饰,先是为她虚增年龄,继而打击假冒福柔帝姬和韦后亲弟韦渊,最后假托神灵庇护,出资建造四圣延祥观以示纪念。但画师们绘制《文姬归汉图》,则是以历史故事来比喻被极力掩盖的事实,揭示韦后生子之事。

图3:仇英《中兴瑞应图》部分,穿红袍站立者为韦后

图4:南京博物院藏《胡笳十八拍》第三拍

图5:波士顿美术馆藏《胡笳十八拍》第三拍
然而,这些传世的文姬题材绘画虽然题材本幅《文姬归汉图》相同,但构图和内容却完全不同。有意思的是,另有一幅现存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传南宋宫素然所作的《明妃出塞图》(图6)。除人物多了两人外,与本图颇为几近相同。此图以昭君出塞为题,纸本设色,尺寸与文姬归汉图接近,落款处题有“镇阳宫素然画”。《宋史·艺文志》及其他宋代文献中均不见宫素然的信息。学界对此图究竟是文姬归汉还是明妃出塞时有争论。

图6: 大阪市立美术馆藏传南宋宫素然《明妃出塞图》
然而,图中的一些元素可以给予一些启示。首先,两幅画作中主人公文姬的衣服很相似,但是《明妃出塞图》中文姬的袖子及身后侍女的袖子明显更宽更长,身前的两名侍从未穿皮裙,而是更宽松的脚蹬裤,这些都是典型的汉族服装特点。其次,侍女抱着的一把琵琶,也是昭君故事中王昭君随身之物。第三,随从队伍的后三人也梳有髡发,但仔细观察可知,他们头顶部还有一簇头发,这不是女真式的髡发而是典型的蒙古式婆焦头法式。最后,这幅画卷的整体构图不如《文姬归汉图》那么紧密和浑然一体,从对人物表情和动物形态的勾勒也可看出动作不够自然,笔法也比较生硬。基于此可大胆推测,此画当绘于宋金之后的元代或明初,其作者的绘画技巧也有限,很可能是学画之人以文姬归汉图为蓝本,在模仿的基础上稍作创新。
《文姬归汉图》与金代女真文化
文姬归汉图是一幅难得的金代绘画佳作,除艺术价值外,该画也蕴藏了丰富的历史信息。自完颜阿骨打1115年起兵反辽到1127年攻陷开封,短短十二年内女真族从东北崛起并迅速占领了包括淮河以北区域的广大地区,建立起了一个包括大量汉族和契丹、渤海等族群的多民族国家。从金太宗到海陵王时期,女真统治者积极借鉴汉族政治制度,吸收汉族文化,逐步建立起了一套以汉文化为主、女真文化为辅的体系。此时的女真内部也逐渐开始分化,一部分搬迁至华北地区的女真人和女真统治贵族已久染华风,而居于白山黑水间的其他女真人,即史称“生女真”,却依然延续着自己的传统。而到了世宗和章宗时期,女真上层忧心于本民族传统的弱化,再次重视女真本族文化,强调注意保持女真旧俗。首先命令皇子贵族练习骑射,告诫他们“女直旧风最为纯直……汝辈当习学之,旧风不可忘也。”继而又颁行女真字经,建立女真进士策、诗会试制度,兼设女真国子学及诸路府学。实际上,这一时期里汉文化影响力却不断扩大,金世宗被《金史》赞为“小尧舜”,而章宗也是“读书喜文,欲变夷狄风俗,行中国礼乐如魏孝文”。至此,女真文化和汉文化在金代后期深度互动,矛盾而融合,但汉文化乃终究渐成主流。
《文姬归汉图》正是创作于章宗朝这个特殊时期。可以注意到,整支队伍中人物的动作表情可大致分为两类。其一类是文姬和她身后的汉族官员,文姬挺直身腰,端庄威仪,目光凝视前方,透出一种坚定而期待的神色。其后的汉官虽持扇遮面,但亦神态自然,面带微笑,毫不为风沙所动。而其余的女真骑士虽身着传统武士之服,但他们都是屈身向前,引袖于头前避风,面露难色。显然,这并非是世宗或章宗所要彰显的女真勇武之风。若依该画之名,则这支队伍是在从北往南的归汉途中,迫使女真武士们退缩又遮掩的一定是来自南方的一阵劲风。
自章宗时起,北方草原上的蒙古诸部快速崛起,在成吉思汗的率领下屡屡突破界壕南侵,不断蚕食金朝在东北和内蒙古地区的统治区域。至1213年宣宗即位时,金朝除中都、真定、大名等11府外,在燕京以北的土地几乎尽失。次年,宣宗迁都汴京,随后河北土地便迅速尽落于蒙古之手。本画诞生于章宗承安年间,正值这场历史巨变的初期。此时,金朝的统治中心已然落于华北,对居于庙堂之上的女真贵族而言,生活于东北的“生女真”已变得异常陌生,几乎等同于汉朝人眼中的匈奴人。
正如艺术史学家卜寿珊(Susan Bush)所说,这种有意识表现出来的文化标签和身份区分,“恰恰是人们期望在1200年左右的金代作品中找到的”。画中的文姬被描绘为一名英雄人物,在形象上和精神上皆显勇敢坚韧,似以此来代表女真传统中的女勇士。但这位女真勇士,却正在走向南方文明的路途上。由此,女真人的自我身份认同以一种反转的方式被展现了出来。在这幅画中,文姬以汉人的身份和装扮出现,却代表着女真。心向汉文化的女真人代表着华夏和文明,而他们的同胞则被描绘成了匈奴人,代表着野蛮和落后。
文姬在逆境和悲伤中表现出的勇气,不仅是简单的凄美,在道德上也具启发性。文姬归汉的故事本身就有彰显忠诚之意,这也是画师想要传递的主要内容之一。作为一名跨越国界的汉族女性,文姬从“文明”的中原来到“野蛮”的草原,多年后又回归故里,如张琳德(Linda Cooke Johnson)所言,可被看作是“文化载体和儒家道德典范”。在一个金代文化日益被汉文化所影响和定义的历史时期中,文姬的形象和含义似乎非常适合该画的观众,即金廷的女真贵族及其子女,因为他们正是生长在这个环境中。由此,我们也可臆测乾隆在画卷上题词时所想。作为12世纪女真人的后裔,清代满人对儒家思想和忠诚概念的理解早已深入,观此画时,想必会不禁联系到自己的文化释读和身份认同。
 关注我们
×
关注我们
×